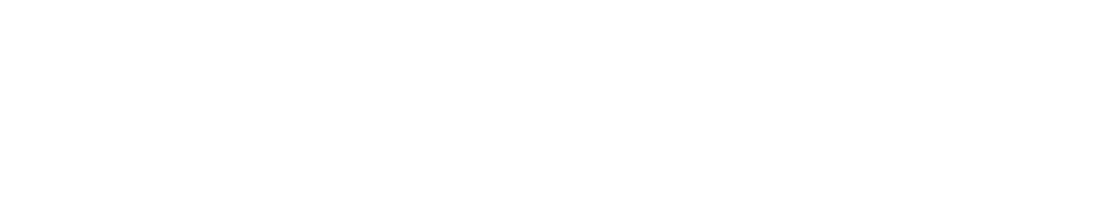院子里,井潭上,墻門邊,一棵偌大的白棗樹(shù)?,F(xiàn)在,又是9月了,經(jīng)歷了最猛烈的盛夏,棗子熟了,有些已經(jīng)有了斑斑點(diǎn)點(diǎn)的土紅。
這棵棗樹(shù),是我老家的新房造好之后,就種植在這里的。回想起來(lái),已經(jīng)有20多年的時(shí)光。當(dāng)初,母親從海島的親戚家?guī)Щ貋?lái)時(shí),它還是一棵小樹(shù)苗。細(xì)細(xì)的枝條,根系倒是挺發(fā)達(dá),看起來(lái)是很能扎根的那種。
母親告訴我,這是白棗樹(shù)。長(zhǎng)出的果子呈肉白色時(shí)就算成熟了,吃起來(lái)多汁而脆甜。
那時(shí)的母親,剛剛完成了造房的大事,里里外外一把好手,顯出風(fēng)風(fēng)火火的樣子。她干著農(nóng)村婦女都干的事,并有著不一般的商業(yè)小頭腦。她很早就開(kāi)始做起了行販的小生意,一根扁擔(dān)兩個(gè)籮筐,走村串巷販?zhǔn)鄹鞣N時(shí)令水果,甚至挑到了隔海的小島。夏日炎炎,她總在行走,甚至顧不上擦一把臉上的汗水。她的心里有一股念想,就是不能讓村里的人瞧不起,要讓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長(zhǎng),供他們讀書獲取知識(shí)。
白棗樹(shù)就一直陪伴在我們的身邊。每年的春天,原本光禿禿的枝干,開(kāi)始長(zhǎng)出密密麻麻的葉條,一點(diǎn)點(diǎn)呈現(xiàn)出綠意,在葉片間默默綻放出米白色的小花直至結(jié)果。到了9月初,它們便有了成熟的模樣。此時(shí),各種鳥(niǎo)兒時(shí)常會(huì)飛聚在枝葉間,不時(shí)地偷啄,間或啾鳴著,整個(gè)院子里便熱鬧起來(lái)。母親忙著干活,進(jìn)出的時(shí)候,有事沒(méi)事地?fù)]手吆喝幾聲,鳥(niǎo)兒便撲棱而散,繼而又聚。
母親是在18年前出的車禍,很嚴(yán)重,術(shù)后恢復(fù)得不好,從此腿瘸了。風(fēng)風(fēng)火火的母親還是閑不住,還在做著力所能及的事,干著農(nóng)活,上街出攤。四五年前,母親的殘腿開(kāi)始肌肉萎縮,行動(dòng)困難,只能臥床了。禍不單行,嚴(yán)重的糖尿病并發(fā)癥,導(dǎo)致她雙目失明,母親也便成了一個(gè)真正的病人,精神也日漸消沉,整日里,昏昏欲睡。
9月下旬之后,樹(shù)上的白棗也基本不見(jiàn)了蹤影,一些已經(jīng)干癟發(fā)紅的棗,味道是不太好的,掉在地上,似乎連鳥(niǎo)兒也不愿搭理。而棗樹(shù)的葉子在瑟瑟的秋風(fēng)里開(kāi)始片片零落,枝干又回到了虬枝零亂的模樣。多像現(xiàn)在的母親啊,她消瘦而微蜷的身軀。只是年復(fù)一年,棗樹(shù)會(huì)重返它截然不同的生機(jī),而漸已病老的母親是再也回不到過(guò)去了。
過(guò)去的母親,牙口好,喜歡吃白棗,常常從地里干活回來(lái),便順手摘幾顆,井水搓洗一下,就往嘴巴里送,一副滿足的樣子。如今,她的牙齒也一顆顆掉落了。一日三餐吃的都是需要磨碎的流食。白棗也咬不碎了,她也不知道是什么,最后還是整顆吐了出來(lái)。有時(shí),只好將棗碾碎了,但母親終究也吃不下幾口汁液了。
樹(shù)下好乘涼,入夜時(shí),晚風(fēng)習(xí)習(xí),星月白亮,井水陰涼。浸了一天的西瓜,冰鎮(zhèn)一般。
這時(shí),推母親出來(lái)靜坐片刻,隨意聊聊過(guò)往的事,有一搭沒(méi)一搭的,不多久,她就暈暈入睡了。間或有個(gè)別的棗掉落下來(lái),打在井蓋上,啪啪作響,多像舊時(shí)光。
棗樹(shù)下,我掛了鳥(niǎo)籠,養(yǎng)著幾只小鸚鵡。還有幾只烏龜,平時(shí)都鉆在陰涼處,一旦喂食,出來(lái)的速度也很快,吞咬小魚的樣子生猛。還有幾盆水生植物,常年青綠著。我希望樹(shù)下一直會(huì)有生活的生機(jī),就像我愿母親還能夠在世上多活幾年。
棗,這個(gè)字,總讓我無(wú)端地想起“早”字來(lái),魯迅讀私塾時(shí)在課桌上刻下了這個(gè)字,是想警示自己讀書不能遲到,做什么事都要趁早。我想,作為晚輩,盡那么一點(diǎn)點(diǎn)孝心,也是應(yīng)該趁早的。